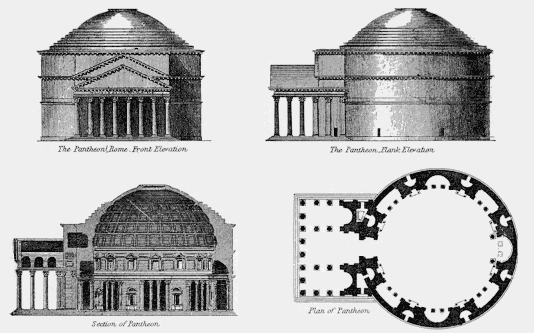AVA Restaurant Slash Bar, 25 Mar 2014
“咦,主菜,是马肉耶!”望着邀请函上的餐单,我充满正义感的友邦惊诧道:“马可是人类的好朋友呀!”
“呃,那,你改主意不去了吗?”朋友试探性的小声问。
“——才没有,”你不知道我是北京人嘛,我们著名的街头小吃,叫驴肉火烧喔——虽然,记忆里我似乎从没吃过……
两周后,朋友忽然传来短讯:“主办方基于公众压力与介意,已决定取消当晚的马肉菜式。”
啊,吃不到马肉啦?那,那转成什么菜?
“鹿肉。”
神马!鹿,也是很无辜很可爱好不好!
我倒是吃过鹿的,还不少次呢。北方人吃鹿的历史似不算长,是自满人习来。故而苏轼识吃,却只是“夢繞雲山心似鹿”,未敢动了邪念;张岱自诩好鲜衣美食,骏马华灯,也仅是羁旅倦客,鹿鹿风尘。但到了清人袁枚那里,鹿就已经是“肉不可輕得,得而制之,其嫩鮮的獐肉之上。燒食可,煨食亦可。”
《红楼梦》里著名的桥段,是湘云与宝玉一起,在芦雪亭烤鹿肉,被人讥笑了就辩驳“是真名士自风流”,以及“我吃这个方爱吃酒,吃了酒才有诗。”烤鹿肉至今在京菜馆里十分常见,后海银锭桥『烤肉季』就有供应。香港也不难找,帝苑酒店里的『东来顺』,黑醋牛尾鹿筋,肉质华美不腻,配红酒绿茶,此乐何及。
我上次吃鹿肉,则是在萨尔斯堡,酒店的餐厅获奖无数,自称走的是“Elegant Cottage Style(高雅乡村风情)”,一笑。供应极好的羊架、兔子及鹿肉,卖相倒十分质朴。酒足饭饱,和不苟言笑却服务熨贴的领班老头聊天,他说比起维也纳,本地文化更受德国影响:“……莫扎特也会自称是巴伐利亚人!更何况,我们这里搭火车去慕尼黑只要一个多小时,到维也纳则要三个钟。我们都觉得自己更像是德国人。”咦,那你们也要全民公投来独立吗?

(图,充满高雅乡村风情的鹿肉,哈哈哈。萨尔斯堡Hotel Goldener Hirsch,2012年冬)
书归正传,晚餐这天终于到啦。主厨是来自意大利南部小镇普利亞的Massimo Santovito,许是被马肉的民众抗议吓坏啦,他决定稳扎稳打的做了道家乡菜:Orecchiette Apulia Style. 鹿肉以小茴香调味,制成茄汁,撒上Pecorino Romano羊干酪。猫耳朵意面的每个凹陷都吸饱了肉汁,七八分熟的嚼劲带出层次感,配有烟草味又辛辣的2011年Rosso di Montalcino,像祖母厨房外婆家,有令游子安心的舒服味觉,不惊,但喜。

这晚的其它菜式也同样欢喜。
甫一落座,侍者奉上白酒一杯,我见是Chardonnay,就即刻扁嘴,不甜!嘬了一小口,果然干的吓人,还满是金属味,立刻丢在一旁。同伴好言相劝,有些酒是一定要配菜哒,比如这个旗鱼刺身,本身是雪藏过的,有腥味,刚刚好能和酒的矿物味中和,鲜甜肥美,咦,托她的福,我竟开始第一次欣赏起dry white wine啦。

(Swordfish Carpaccio)
主菜是红酒山鸡煲。邻座很渊博的一位食家,乍见调味用了黑松露,马上复刻我见到Chardonnay白酒时的失落感,摇头嘟囔说:“我讨厌一切香菇的亲戚们,它们气味霸道,鸠占鹊巢,喧宾夺主……”哼,你妈妈煲汤时候落了虫草、灵芝,你也不肯喝吗,我揶揄他。可见,我对松露,是真爱呀。

(Pheasant Stew)
用了肉桂调味的山鸡,本身是不错的,但肉质紧实,我嫌它口感太纤维化,干干巴巴。反而是配菜的甜栗子和胡萝卜,前者缠绵后者干脆,又带着馥郁的松露味,刚好配得起2009年的Brunello。
餐后甜酒是Vendemmia Tardiva,甜牙齿迫不及待尝了一口,唔,味道好怪,甜酒竟然也有很多层次,而且有点中药味儿是怎么回事儿?好像,我还是比较喜欢我的老相好Passito di Pantelleria喔……
好吧,人生总要move on。当我兀自腹诽的阵儿,甜点已然上桌。甘草味儿的奶冻,配甘草和黑橄榄的雪糕。神马,橄榄雪糕,你是暗黑料理吗?我并不憎恶甘草,虽然也远远谈不上喜欢,它和罗汉果一样,甜而带着不易亲昵的中药味,对,中药味,我忽然想起来,忙喝了一口酒,咦,好般配,你们是失散的兄妹吗!于是,醇厚甘甜又带点小小果香的甜酒,与甘草味道雪糕里嵌入的青涩韧劲的橄榄,以及几颗小小的覆盆子,真是充满心机。您就是解构艺术的先锋呀!

(Due of Liquorices Panna Cotta & Semifreddo of Chocolate and Black Olive)
于是不明不白的,我竟然伴着甜点,喝光了那杯我原本并不喜欢的甜酒。再次印证朋友的谆谆教诲:“喝酒要配菜,打狗看主人!”咦,酒过三巡,思维似乎也奔腾起来。
这惊喜的甜点让我们一致策动要把厨子抓出来拷问,他彬彬有礼前来问安,而后介绍,甘草橄榄雪糕,果然是他为那甜酒而特地创作哒。“其实几年前,我就开始帮iScream设计他们的新口味雪糕啦,反向还不错呢。” Massimo Santovito来香港两年,此前则一直在伦敦为厨。香港人的口味与欧洲有不同吗,你需要迎合吗?
“迎合是必要的呀,客人们开心是最重要的。”
他这观点和当晚酒庄的代理人Conway竟然不谋而合,我说你这样钟意饮饮食食的人,把它变为一项事业,是不是太认真啦。他笑答迎合并不代表不忠于自己的喜好啊,倒是充满禅意。